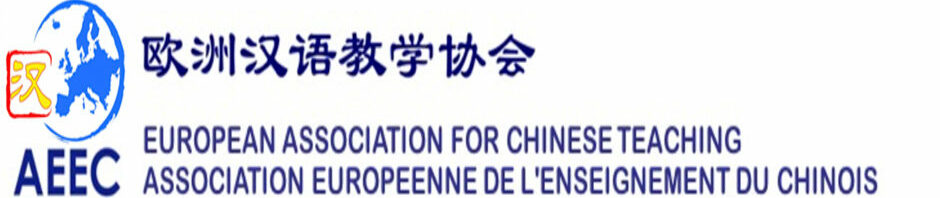缅怀法国伟大的汉学家汪德迈先生——法国国民教育部荣誉总督学白乐桑访谈录
ciglobal
从语言入手,用文化交融,促民心相通。
CI CLASSROOM
孔/院/微/课/堂
CI CLASSROOM
(本文转载自《孔子学院》中法文对照版2021年第2期/总第62期)
李晓红:白教授好!请您谈谈您和汪德迈先生的缘分,您认为汪德迈先生对法国汉学的贡献是什么?
白乐桑:一般来说,我不太习惯按照拟好的问题谈,但我想,我以下所说的也许能回答你的问题。
汪德迈先生仙逝的日子将写入法国传统汉学史的史册。
汪德迈先生的离去,意味着伟大的法国传统汉学宏大宽阔帷幕的落下。某种意义上是说,汪德迈先生是最后一位故去的伟大的法国汉学家。这并非说,他身后就没有汉学的专家,法国汉学也会继续发展,法国汉学会后继有人。但是,汪德迈先生作为法国传统汉学的旗帜,倒下了,我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汪德迈先生如同他的老师戴密微先生(Paul Demiéville, 1894–1979)、太老师沙畹(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 等汉学家都是严格意义上的汉学家。说到汪德迈先生的成就,我就常想到沙畹先生,他与汪德迈一样,专攻汉学里的哲学,也可以说,汪先生的学识来自他的老师、太老师,我们将会把他与戴密微、沙畹联系起来看,因为他是他们“直接的知识科学血统”的一部分。为何我们称他们为汉学家?是因为他们的成就、他们所研究的诸项成果覆盖了法国汉学界各个不同的领域,使今日法国汉学形成兴盛的局面。
如今,在汪德迈身后,法国新一代汉学家正在成长,他们以各自的专长朝向学院派的高度继续迈进,继往开来,开创新局面。比如,我们现在就在索邦大学白莲花(Flora Blanchon, 1943–2012) 教授(CREOPS) 的办公室里谈话,她是汪德迈学生之一,又是您的博士导师,以考古艺术史为长。汪先生的学生里还有宋史专家、汉语语言学家、当代文学专家、唐诗研究专家等。这都很正常,因为汪先生很博学,他的研究领域几乎覆盖了汉学的所有领域,他的这些专长传承给了他很多学生,所以法国汉学一直在发展。
我再回到汪先生本身,他是一位伟大的汉学家,我们都很荣幸与他相识。也许,他是法国最后一位汉学代表人物。汪先生专长于儒学和中国古代文字,这两个领域可以说是他对世界汉学界最重要的贡献。汪先生还对汉文化圈国家的汉学研究有深层思考,他还对道德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等研究感兴趣。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新的汉学时代,汪先生曾经研究过的任何一个门类现在都有可能成为汉学的一个分支。比如,我们有研究甲骨文的专家,可是,他们也许只专长于甲骨文,这并非说这些学者的研究面很窄,因为今天在学界几乎所有学者都是某一门类深入研究的专家。汪先生的研究领域太广了。所以,从这点来说,汪先生身后再无汉学家。
我不知道您是否发现,法国的汉学家不敢自称汉学家。当您问他们时,他们往往会说:“我是宋代历史学家”;若问我,我会说:“我是中文教学法专家”。当然,我不排除有人会说自己是汉学家,但是至少我们不会这样自称。因为我们意识到这里的演变,这里的“演变”其实是指汉学或称中国学在朝向更细的专业化方向发展。从传统的法国汉学来说,这些前辈汉学家造诣都很深,既能精通儒家学说,又通晓中国古文字( 甲骨文),达到很高的学术水准。您看,汪德迈先生和沙畹一样,他们既走进了最高深度的文字学殿堂,又走进了最高深度的哲学殿堂,还能够达到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体制等核心领域研究的高度,做汉学如同探囊取物。
我们都知道,在汪老晚年,您与他关系密切,您是不是正在做他学术思想研究的访谈录?
李晓红:是的,近三年来,我与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欧明俊教授有一个计划,共同来做汪德迈先生学术思想访谈录的工作。
白乐桑:很好的计划,是抢救文化的重要举措,因此您与他交谈的机会比较多。我感觉,您就可以说:“我认识了‘末代’汉学家!”我们知道有广义的“汉学家”,有狭义的“汉学家”,甚至有时候有人不是真正的专家,或是没有在大学教过书的,都自称“汉学家”,这种所谓的“汉学家”是一种不妥的叫法。
汪德迈先生是一位杰出的、伟大的汉学家。
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位专家能像他那样,让人们关注到中文、中国文字,是汪先生开启了文字研究之门,他是法国汉学界第一位对甲骨文进行学术研究的学院派的专家,是他如此深入、全面地关注和研究中国文字的性质与中国文字的书写。他的作用是非常伟大的!我平常慎用“伟大”一词,可是为了形容汪先生的学术贡献,我毫不犹豫地运用这个词。我说他伟大,不只是因为他是传统意义上的汉学大家,而是由于他破天荒地开创性地阐述了中国文明最本质的问题,就是甲骨文及中国文字的性质。这一建树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几乎从一开始,就轻视文字和书写,或者说,他对文字的看法是很狭隘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文字( 指西方表音文字) 只是记录语音,文字是为语言服务的。索绪尔对汉语只说过一句话:“对于讲汉语的人来说,文字是第二语言。”我发现很少有人去评论他的这句话。当然,就是这句话反映了索绪尔意识到中国文字的独特性。而在理论上,汪德迈先生借用了在甲骨文上的造诣,在中国文字的独特性上立论,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点。
在中国文明的基因里,文字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中国文字在中国思想、中国文明、中国艺术等领域打下了非常重要的烙印。对于中文最本体的“字”的问题,汪先生有着卓越的贡献与论述。曾经有些汉学家也分析过,但没有像汪先生分析得那么透彻,尤其是对文言的分析。汪先生之所以伟大,是他对语( 语言) 与文( 文字)的关系研究得深,是他填补了语言学的空白,他是反潮流的。如果是西文的话,语言包括文字,因为记音,因为分析语音的需要,而文字只是一个简单的工具而已。现代语言学就是想分析描述语言现象,而把文字的问题放在很边缘的位置。
我编的教材坚持“字本论’, 获得汪先生的支持。
我编的教材Méthode d’initiation à la langue et à l’écriture chinoises (《中国语言文字的启蒙》),1989 年底问世,我没有料到的是,在中文国际语言教育学领域产生了一番很大的学术辩论,学者们对我的“字本位”观点与所谓“词本位”观点争议很大。记得当时,我寄书给汪先生,他竟然给我回了信。那个时代的所有汉学大家,不论是谢和耐还是汪德迈都是研究古典学问的,但是他们都非常重视中文教学。在汪先生的信里,第一,反映了他的重视,他说:“您的教材的问世,是法国汉语教学里的里程碑。”第二,他特别告诉我说:“我本来学习中文,多么希望有这样的教材。”汪先生看到了我“把‘文’放到应有的位置”,“把‘字’放到应有的位置”的观点,他对我表示支持。然而,我是晚辈,而且研究的是中文教育,我因此非常感恩。
您知道,我是何时了解汪先生对中国文字的观点吗?我第一次认识他,是1979 年在巴黎第七大学,那里办了一个关于文字研究的研讨会。后来出了一本论文集,里边有汪先生的一篇文章,我跟他说:“从那时起,您关于文字的重要观点激发了我的兴趣。您的思想很宏观,与我的中文教育有呼应作用。”我当时发现,中文教育有一个很大的空白,是在中国出的教材( 对外汉语) 里,从最先开始,他们就否认“字”作为最小的语言教学单位的存在,也没有意识到“语”( 口头语) 和“文”( 文字) 有相对的独立性。比如,他们认为,“中国”一词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中”和“国”两个字其实是表意单位。所以,我认为对外汉语的学者很矛盾,一方面说中国是表意文字,而另一方面在教材里边,不给单“字”释义。那么,这表意文字如何体现呢?
我拜读过汪先生的法国国家博士论文《王道》,非常佩服,这篇博大精深的论文涵盖他对中国古典社会体制、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中国古代文化的理解,也涵盖他对儒家学说的认识。在书的前几页,他对甲骨文的性质还进行过透彻的阐述,完全证明了我开场白的看法。我是在1979 年、1980 年读到汪先生关于文字的研究以及中国文字性质独特的论述的。所以,我说汪先生伟大,令人无限敬仰,是由于他很早就发起并开展了对甲骨文的研究、对中国古文字性质的研究,而不是在晚年。
他的法国国家博士论文《王道》是什么时候开始动笔的?我真的不知道,您知道吗?
李晓红:我们有过研究,我和欧明俊教授撰写的《汪德迈先生学术访谈录》里谈到过这些。1954 年,汪先生在巴黎大学注册修读法国国家博士资格。这篇论文写于汪先生在日本留学期间,1966 年他回到法国后继续撰写并完稿。1975 年他通过答辩,获得国家博士学位,指导教师为谢和耐,汪先生时年47 岁。
白乐桑:汪先生了不起。也就是说,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的法国汉学家里,包括汉学前辈中,他是唯一一位甲骨文权威,是严格意义上的权威。他对甲骨文的研究、对中国古代文字性质的研究,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
哲人其萎,风范长存!
汪德迈先生精神必将与日月同辉!
//
白乐桑:法国教育部首任汉语总督学,法国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副会长,欧洲汉语教学协会会长,法国著名汉学家。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访问《孔子学院》官网获取。
地址:https://www.ci.cn/#/detailBanner/Publication/
推荐阅读
1 | |
2 | |
3 | |
4 | |
5 |
作者:白乐桑 Joël Bellassen 李晓红 Li Xiaohong
图文排版:贾舒清(实习)
点击 阅读原文 ,查看《孔子学院》期刊征稿函,欢迎踊跃投稿!
Scan to Follow
use this Mini Program